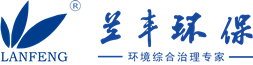歲末年初,電影《芳華》大火,有人看到了似水流年、青春回憶,有人緬懷了一個叫文工團的團體,也有人感慨歲月易逝、好人難做。又看了嚴歌苓的原著小說,電影之外,多了一分對人性幽暗和明媚的追問和思考。
電影的英文名是Youth,是青春,是芳華,書的英文名是“You touched me”,有兩層意思:一層是你摸了我,劉峰對林丁丁的“觸摸事件”直接改變了學雷鋒標兵劉峰的人生走向;一層是你感動了我,劉峰對小曼的仗義伴舞陪練托起了小曼的身體,也打動了她的心,以及青春逝去、潮流更替、境遇變遷下劉峰、小曼等人的經歷引起“我”的感動。

一口氣就可以讀完小說《芳華》,感覺就像嚴歌苓講了個故事,而我們像聽她講了一個故事,文字精練優美、善用比喻、幽默詼諧、帶鏡頭感。
《芳華》的文字是詩意的。開頭描寫多年后遇到劉峰,“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臉龐的腦海里,我的視線瞬間就把他釣出水面”;描寫何小曼,“何小曼整個人可以忽略不計,就那雙眼睛長對了,黑的像秘密本身”。
善用比喻,描寫小曼孤苦、凄涼的后爹童年,“保姆說小曼就像她村里的狗,找到一塊骨頭不易,舍不得一下啃了,怕別的狗跟它搶,就挖個坑把骨頭埋起來,往上撒泡尿,誰也不跟它搶的時候再刨出來,篤篤定定地啃。”

嚴歌苓不僅是小說家,也是知名編劇,文字帶有很強的鏡頭感,比如說劉峰打靶場抓起“我”,“我似乎是認識這張臉的,但因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寫而顯得陌生”;再比如回憶中的劉峰的出場,“紅樓的二層三層帶長廊,長廊上面張著長長的廊檐。假如你傍晚在三樓走廊上吹黑管或拉小提琴練習曲,目光漫游,越過樓下也帶廊檐的回廊,再越過回廊盡頭的小排練室,繞過小排練室右側的冬青小道,往往會看到一個挑著倆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劉峰”。
巧妙的敘述方式,寫多年后劉峰和郝淑雯的海南相遇,“劉峰跟郝淑雯本來不該碰上的,兩人的社會相隔無數層次。假如那天劉峰不去找城管頭頭討要他的三輪汽車的話,假如那天郝淑雯不是到同一條街上的俱樂部去找打牌打了兩天兩夜的丈夫的話,假如劉峰不是在俱樂部對面等待城管頭頭從洗浴房出浴的話,假如不是郝淑雯的老公打發她回家取現金付賭債的話,假如不是劉峰等絕望了跟攔阻他的洗浴房門衛大聲爭起來的話,他們倆都不會碰面,就是擦肩而過也會錯過去。”用幾個假如,很快勾勒出兩個人物的多年際遇變化和當前狀態。
嚴歌苓在凝望芳華,也在凝視人心。盡管是虛構的故事,她坦言,這是她最誠實的一本書,“我講了大量的真話,也講了很多我對當年的一些戰友,尤其是何小曼這樣一個人物的懺悔,以及很多對青春里發生的一些現象的反思”。
對“混賬”時代的反思,“我父親在水壩上扛活六七年,從聽別人講他壞話,到自己講自己壞話,再到他重獲講別人壞話的資格,什么能再洗去他的卑鄙換回他最初的純真?大半個世紀到處都講別人壞話,背地的、公開的,我們就這樣成長和世故起來”。
對自我的反思,甚至批判,雖不激烈,卻有捫心自問的深刻。觸摸事件中林丁丁的心理分析,“我們由于人性的局限,在心的黑暗潛流里,從來沒有相信劉峰是真實的,假如是真實的,像表面表現的那樣,那他就不是人,哪個女人會愛上不是人的人呢?”眾人對劉峰反目孤立的反思, “一旦發現英雄也會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會格外擁擠。”
但小曼愛上了劉峰, “她活了二十多歲,一路受傷到此刻,她的一路都是多么需要陪伴和慰藉,這她最明白。那天晚上,其實小曼想告訴劉峰,從那次托舉,他的兩只手掌觸碰了她的身體,她的腰,她就一直感激他。他的觸碰是輕柔的,是撫慰的,是知道受傷者疼痛的,是借著公家觸碰輸送了私人同情的,因此也就絕不只是一個舞蹈的規定動作,他給她的,超出了規定動作許多許多。他把她摟抱起來,把她放置在肩膀上,這世界上,只有她的親父親那樣扛過她。在排練中和演出中,她被他一次次扛著,就像四歲時父親扛她那樣,讓她感到安全,踏實,感到被寶貝著,感到……那一會兒她是嬌貴的,是被人當掌上明珠的。明天,抱她的人就要走了,再也沒有這個人,在所有人拒絕抱她的時候,向她伸出兩個輕柔的手掌。”

電影看完,沉浸在《絨花》的歌聲里,我們緬懷芳華歲月,雖然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是如此不同;掩上封面,呆如木雞,久久不能平復,當芳華褪去,留下什么,善良如劉峰,倔強如小曼,人散人聚,時光流轉,還能感覺一點點溫暖和勇敢,便知心中芳華還在。
品牌建設部 楊國松
 |
|